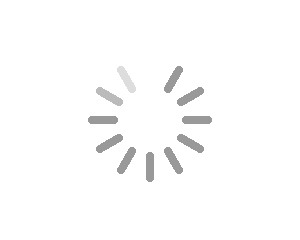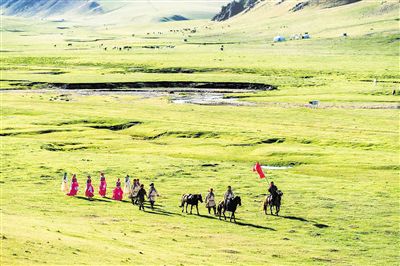监督意见经充分调查论证,检察机关认为,案涉借贷行为系某滨集团与某航小贷公司为规避金融监管政策、协商一致形成,朱某等三名员工系受某滨集团委托向某航小贷公司借款,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均是某滨集团。某航小贷公司明知案涉借款是某滨集团委托其员工以个人名义办理,本案应适用委托关系的法律规定认定由某滨集团承担还款责任。2021年3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就朱某与某航小贷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并指令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朱某仍承担还款责任。朱某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某航小贷公司向法庭提交《关于朱某申请贷款1000万元的信贷调查报告》,报告载明“朱某个人从事海参养殖加工销售行业,年经营收入3000万元左右,年获利1000万元左右,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但该公司并无朱某从业经营资质、经营场所、生产经营财务报表、贷后检查工作日志记录等证据佐证朱某借款事实存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以在案证据结合某航小贷公司出借款项数额巨大、不知借款人资信情况、对出借资金放任失管及对特殊行业贷款实施金融监管等多种因素,认定案涉借款系某滨集团委托公司员工以个人名义向某航小贷公司借款,某航小贷公司对案涉借款人为某滨集团的事实明知,按照委托关系的法律规定确认还款责任主体为某滨集团,判令朱某不承担还款责任。2023年3月,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将侯某辉、程某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提请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2023年8月,两案再审均改判侯某辉、程某不承担还款责任。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借名贷款”案件中,应综合案件事实,准确适用委托关系相关规定,依法认定责任主体。“借名贷款”系指实际用款人借用他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办理贷款手续,所贷款项由实际用款人使用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对此存在认定分歧。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中,应综合合同签订、履行等事实,准确认定责任承担主体。一般而言,出借人系基于对名义借款人身份资格、资信能力的信赖出借款项,基于合同相对性及意思自治,应认定名义借款人为合同主体、承担还款责任。出借人在出借资金时明知借款人所借款项是由实际用款人使用的,应着重审查出借人是否明知名义借款人系受实际用款人委托借款,结合出借方属性、借名目的等,正确区分名义借款人系“代理实际用款人借款”或“为实际借款人借款”,准确适用《民法典》关于委托关系的相关规定,认定责任主体。参考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商业银行作为出借方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知道实际用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出借方和实际借款人。本案出借方作为小贷公司,其签约时明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为规避金融监管、实现将政策性扶持贷款违规发放给实际用款人的目的,与实际用款公司委托的公司员工签订借款合同,各方对于真实借款主体意思表示一致,案涉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小贷公司与实际用款人,应由实际用款人承担还款责任。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注重运用一体化办案机制,强化案件调查核实,切实提升监督质效。“借名贷款”案件中,合同签订等事实对于认定出借方是否明知名义借款人系代理实际用款人借款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市、区两级检察院成立一体化办案团队,围绕争议焦点全面梳理案件事实、开展调查核实,准确分析研判案涉法律适用问题,剖析出借方与借款方公司及该公司员工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提升办案质效。公司员工以其个人名义为公司向小贷公司借款,其自身未尽相应注意义务应受否定性评价,但在出借方系为规避金融监管、明知公司员工系受公司委托借款之情形下,通过依法监督让劳动者摆脱巨额债务,亦体现民法典平等保护的精神,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例五
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与宋某坤、山东某物流有限公司、某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抗诉案
关键词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交通安全统筹数字检察社会治理
基本案情
徐某芹系陈某善之妻,陈某晓、陈某强二人之母。2021年4月12日,宋某坤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车主为山东某物流有限公司,实际车主为葛某)与徐某芹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致徐某芹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宋某坤负事故主要责任,徐某芹负次要责任。同年9月8日,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诉至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调解或判令宋某坤、山东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流公司)、某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526854元并承担诉讼费。
莒南县人民法院认为,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请求某物流公司赔偿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肇事车辆在某科技公司投保金额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险,因本案交强险部分已达成和解,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应由某科技公司承担70%。故判决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超出交强险的剩余损失(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共计749850.50元,由某科技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赔偿限额内赔偿524895.35元。
判决生效后,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向莒南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因某科技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莒南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向莒南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莒南县人民法院逾期未作出裁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受理及审查情况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向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主张在案件执行时得知某科技公司濒临破产无执行能力,莒南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原审将交通安全统筹等同于商业保险错误。莒南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审查后,提请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检察机关通过调阅卷宗、调取交通安全统筹单、询问当事人等,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审查:一是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检察机关受理条件。一审判决生效后,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未提出上诉,系因其赔偿请求得以支持,无提起上诉之必要。后在执行过程中方知权益无法实现,此时已过上诉期,转而申请再审符合受理条件。二是案涉车辆参统的交通安全统筹是否等同于商业第三者险。综合调取的交通安全统筹单及某科技公司的营业执照查明,某科技公司经营范围为物联网交通安全统筹等业务,并未取得保险业务经营许可,案涉车辆参统的交通安全统筹并非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三是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应由谁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系一般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由肇事车主按照过错承担侵权责任,但为了更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保障,保险制度得以设立。在保险制度的大背景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确定的赔偿顺序为“机动车强制保险—商业保险—侵权人”,此处的“侵权人”包括挂靠车主和被挂靠的物流公司。交通安全统筹合同作为统筹公司与参统人员的协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按照合同约定予以确定。
监督意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涉及的交通安全统筹的性质认定及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审查之后,认为生效判决认定“肇事车辆在某科技公司投保保险金额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险”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确有错误,遂于2023年5月19日向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监督结果2023年6月8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莒南县人民法院再审。再审中,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要求追加实际车主葛某参加诉讼。莒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告知陈某善、陈某晓、陈某强可另行起诉。
延伸工作在开展生效裁判结果监督的同时,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提升监督质效。一是强化数字检察思维,构建“机动车辆安全统筹业态治理类案监督”模型,共收集数据5000余条,涉及营运货车1161辆、运输企业218家、统筹企业81家。模型推广应用后,已发现案件线索13件,办理监督案件2件。二是凝聚检法共识,与人民法院召开工作联席会,统一交通安全统筹领域案件裁判尺度,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三是参与社会治理,向莒南县交通运输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开展专项行动,化解风险线索13条,助推行业管理和诉源治理。四是推动成果转化,形成道路交通安全统筹领域社会治理问题专项调研报告上报市委市政府,以“检察专报”引导动态防治。
典型意义
一)检察机关在办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监督案件时,应当核实所涉法律关系,合理确定各方责任,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究明法律关系和责任原理,是准确适用民法典进行法律监督的基础和关键。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要查清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挂靠关系,是否购买交强险、商业保险等问题,进而准确适用《民法典》相关条文,确定各方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交通安全统筹合同的性质及法律适用在司法裁判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统筹合同等于商业保险合同或者类比保险合同,统筹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二是统筹合同不是商业保险合同,应按照一般合同纠纷进行处理;三是统筹公司违反《保险法》规定,为无效合同,应按照过错原则确定统筹双方责任。本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案件明确交通安全统筹合同并非保险合同,而是一种行业互助举措,当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应由统筹人直接赔偿受害人损失,而是应当根据《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确定侵权人责任。二)检察机关在依法办理案件的同时,要通过大数据赋能加大监督力度,实现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检察机关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道路交通安全统筹案件多发、监管机制不健全、法院裁判尺度不统一等问题开展专项调研,通过建立数字监督模型,以大数据赋能深入发现案件线索,加大办案力度,凝聚检法共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研究破解社会治理难点堵点,督促行政机关加强监督管理,防范风险问题的发生,实现了从个案监督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以检察履职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统筹业务良性健康发展,提升了法律监督质效,展现了参与市域现代化建设、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检察担当。案例六
王某夫与某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检察和解案
关键词
金融借款合同抵押范围民法典适用检察和解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昆明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商贸公司)与昆明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以下简称某农村信用社)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某商贸公司向某农村信用社借款1500万元。同日,某农村信用社与王某夫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以王某夫名下昆明的一套房产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作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登记他项权证上记载“被担保主债权数额365万元”。2016年11月,某农村信用社与某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某资产管理公司依法受让债权及从权利,成为新债权人。2020年1月,因某商贸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某资产管理公司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商贸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合计2400万元,王某夫在抵押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抵押责任。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商贸公司未按期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构成违约,王某夫与某农村信用社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已依法成立,抵押权随主债权转让,某资产管理公司有权对王某夫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王某夫不服一审判决,认为抵押登记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不一致、一审判决以《抵押合同》约定内容判定案涉抵押物担保范围适用法律错误,遂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文章来源于:http://www.kzrd.com 快照热点
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其真实性与本站无关,请网友慎重判断